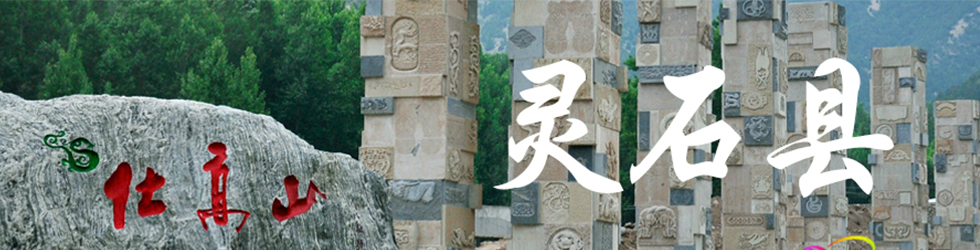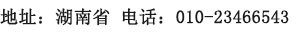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选自《中原文物》年01期,田建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摘要: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辿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一任何一个遗迹现象、一座墓葬,一旦发掘清理,就不复存在,这个道理不说也明白。对遗迹和墓地进行的完整考古报告,就如同记录片一样,使我们能够看到“情景再现”,随时可以进行全面研究;而大多只挑重点报道的简报,充其量只能算作是“片段记忆”,以满足人们短期研究之需。倘若发掘者将简报作为报告对待,则会给学术界造成损失。206年9月出版的《灵石旌介商墓》发掘报告①,就完成了从简报到报告的飞跃,发表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资料。众所周知,1976年和1985年两次共清理的3座灵石旌介商代晚期大墓,已有简报发表,即《文物资料丛刊》3的《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及《文物》1986年1期的《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20多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依据就是这两篇简报。关于该报告写作的特点或优点,尽管李伯谦教授在序中所述已备,但我还是要说,报告编排形式新颖大方,又简单实用。表现在:1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发现、发掘与研究概况;下编为出土青铜器的综合考察,墓葬的时代与性质。编者将报告发掘记录与研究体会分开,体现了苏秉琦教授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考古报告是十三经,研究文章是十三经的注疏部分”。2每件器物一般按彩色照片、线图、拓片、X线片排列,尤其是每件器物线图下,附有这件器物的数据表,与以前考古报告中不厌其烦的文字说明相比,后者显得一目了然。《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将M1、M2时代定为“殷墟晚期,或者在商周之际”。《灵石旌介商墓》则认为:M3的年代应该稍早于M1,而M2应当最迟。但最早的M3年代大概相当于殷墟四期之初的文丁时期,而M1居于其后,M2则延续至商周之际大概在帝辛之末。于是乎,成一家之言。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该报告在极个别地方仍出现有少量叙述不当或自相矛盾之处:1在M1随葬品位置介绍中,棺内“墓中随葬品除出土于上述位置以及腰坑内的,大量的随葬品均位于三棺之中或三棺之上”。导致如鼎标本M1∶26“出土于右侧女墓主人的头部”之类的不正常位置。先秦时期除非个别情形,一般铜容器是不会放在棺内随葬的。M2也存在类似问题。2下编第一章“出土青铜器的综合考察”中,第二节“青铜器的纹饰特征”归类为E型的蛇纹“见于鼎M1∶36颈部,觚M1∶14颈部”。在上编“墓葬概况及随葬情况”第一节“M1”中,经查对,鼎M1∶36颈部饰一周12只卷尾蛇纹,呈逆时针方向排列。而铜觚M1∶14,“形制大小及纹饰几乎同M1∶20。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标本M1∶14的蚕纹呈逆时针,而标本M1∶20的蚕纹为顺时针方向”。M1∶20“颈部饰四瓣倒置蕉叶纹,蕉叶内饰倒置的分解式兽面纹。兽面纹直角内卷,圆形眼。颈下饰一周曲体蚕纹,蚕尾向内卷曲”。前后名称没有统一。3下编第一章第三节“青铜器的铭文特征”中,九种铭文(族徽),除两种没有隶定外,其余都是今天的常用字,没有必要用英文字母表示,尤其是放在图表里,不如直接用铭文(族徽)更能显示清楚。在“青铜器的徽识反映的族属情况”部分,丙族(国)最后出现更显得突兀。4《灵石旌介商墓》图94陶鬲M1∶25,线图剖面不在人们习惯的和本报告其他线图一样的左边,可能属编辑的问题。以旌介商墓的全部资料为契机,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进行梳理。二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发现和发掘的遗址、墓葬并不多②。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清理了1座陶窑和35座灰坑。报告说:“基本同于安阳殷墟的商代文化,时代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到二期……没有超出殷墟遗址出土的陶器。这些情况表明小神遗址所在的长治地区当时处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③小神遗存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④,遗址分布仅有很小面积,但发现一座房子ⅠF1,出土有卷沿深腹鬲、小口罐、敞口盆。由敞口盆“腹部阴刻弦纹两周,其间分隔成正倒三角形界格,正三角形减地磨光,倒三角形平面凸起,饰绳纹”看,也可能是簋,年代在商代晚期,报告中以“殷墟文化遗存”介绍。该地向来与洛阳关系密切,所以也处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山西自灵石口以南地区,过去调查发现有运城长江府、临猗黄仪南村及临汾盆地的临汾(今尧都区)大苏⑤等一些零星遗存。年5月在襄汾南小张清理一灰坑⑥,无复原器物,年代为殷墟一期,正式报告还未发表。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与灵石旌介同处太岳山的临汾庞杜⑦和浮山桥北⑧,分别于202和203年发掘出商代墓葬,其中桥北有5座带墓道的王侯级大型墓及9座中型墓,年代与旌介差不多。相比之下,晋中地区和吕梁山一线,发现商墓较多。晋中地区的发现是从灵石旌介商墓开始的。旌介商墓,文化因素构成较小神要复杂得多。正如李伯谦先生认为的那样⑨,旌介商墓以大量的铜容器为代表,包括器形及其组合,和相当一部分铜矛、戈、弓形器及玉器、骨器等,表现出完全的商文化特征,“灵石旌介墓葬以A群铜器为代表的因素,与殷墟相同或相近,又是其主要成分,占有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来看,它应该属于商文化系统”,“属于B群的铸造粗糙的圆饼纹铜鼎、透雕羽状三角援铜戈、侈口筒腹瘪裆陶鬲少见或不见于殷墟”。M1随葬23件青铜容器中,带铭文器16件,其中带有“”族徽的有爵、卣、罍共1件;M2随葬18件青铜容器中,就有鼎、簋、罍、觚、爵共17件及铜矛2件共19件铸有这个族徽;M3出土铜器虽已散失,但带有“”族徽的也有鼎、爵、卣,共4件。毫无疑问,这3座墓葬,主人是“”族(国)的首领。至于它是不是“丙国”,那是另外的事情了。邹衡先生把“”,视为分裆鬲族徽⑩,旌介M1、M2还没有发掘之前,他已经收集到这种族徽10件左右了。出土地点明确者有陕西扶风北桥、歧山贺家村、长安马王村,河南洛阳、安阳孝民屯、郏城,北京琉璃河,山东黄县,辽宁喀左及山西灵石旌介(M3)等18器,时代约在殷墟四期至西周穆王之前。看来,“”族在商周之际是相当活跃的。稍后,殷玮璋、曹淑琴先生在《灵石商墓与丙国铜器》中瑏瑡,统计出有“”的铜器达170余件,他们将时代定为商代武丁至西周早期康昭之世,立国30余年。而《灵石旌介商墓》是采用王晖先生的意见瑢瑏,推测“丙国或丙族可能就是商代存在的十干氏族之一的丙族”,就是商族。其实,在王晖的文中判定“十干氏族”主要是根据大量的殷墟卜辞,但“丙”国的例证并没有一个出自卜辞,都是商代金文;况且,“《续殷文存》下182著录一爵,下有一亚框,带有亚形的族徽可能是商王朝异姓方国的标志”瑏瑣。及殷墟不见而见于旌介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差异等,都说明“”族是否为“十干氏族”还需深究。但不妨碍“旌介商代晚期墓葬应当归属于商文化系统,同时又是区别于中心区商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瑏瑤。彻底解决旌介的问题,还得从最具有普遍意义的陶器入手。旌介商墓仅有两件陶鬲,但随葬的位置不同。由《灵石旌介商墓》图6“M1墓室平面图”清晰可见M1∶25与鼎、斝、觚、爵、觯等大宗铜器随葬在一起,标志着其为墓主人所有。M2∶4陶鬲出土位置,“墓圹填土中”一节介绍得相当清楚。“墓室西北角距墓底09米的填土中出土一具男性人骨架,除盆骨、股骨、指骨和趾骨保存较差外,其余部分保存尚好。葬式为仰身直肢,在其胸部发现一枚贝。头骨被分成两半,应该是被处死后作殉葬的。在墓室东部出土一完整的牛腿骨,也应是将一条完整的牛腿进行殉葬的。在墓室东部正中出土牛腿骨附近还出土一件陶鬲。”并附有图105“M2墓室”,清楚地显示了这件陶鬲和殉人、牛腿骨在熟土二层台上,它们跟椁内、棺外的大量随葬品,包括带有“”族徽的铜矛M2∶5、M2∶23等截然不同。后者属墓主人所有,前者属于殉人所代表的群体。三灵石旌介位于晋中盆地南部,这个地区商代晚期分布着“杏花类型”瑥瑏,除旌介外,还有汾阳杏花和太谷白燕等。《晋中考古》“结语”中,将杏花Ⅶ期2段,即杏花类型,解析出三个谱系的陶鬲,即商式鬲、本地传统的陶鬲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形鬲。“后者,无疑是在本地传统形鬲的基础上,接受商式鬲的某些特点的影响的产物”,“区别于一、二两谱系的另一谱系的陶鬲”。就是说,二谱系的鬲分传统形和中间形两类。这次发表的旌介两件陶鬲,线图和照片均比较大。M1∶25,卷沿,圆唇,矮领,腹部斜直,略呈筒形,瘪裆,袋足;麻点状绳纹;灰褐色夹砂陶;M2∶4,圆唇,宽折沿,直领,腹部微鼓,袋足,分裆,裆低矮;器表饰交错粗绳纹;夹砂灰陶。分别属于一谱系和二谱系的传统形,可与杏花墓地M29∶1、M62∶1(图一三五:17、《晋中考古》图一三四:5)相比较。(图一、图二)按照商式鬲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实足跟越晚越趋于矮小至无,裆越低。很显然,杏花墓地M29∶1要早于旌介M1∶25。而杏花还有更早的商式鬲,如M1∶1、M26∶1(《晋中考古》图一三四:1、图一三五:2)等。《晋中考古》只是说M71在Ⅳ区的断崖上,在图七八“杏花村遗址分区示意图”没有标出,不知这座墓可否归属相邻的Ⅴ区杏花墓地。无论如何,杏花村出自墓葬的二谱系鬲,可分三组。第一组,M71∶2(《晋中考古》图一三〇:14)传统形和M71∶1(《晋中考古》图一三〇:1)中间形,各自特征明显(图二);第二组,M4∶1(《晋中考古》图一三四:6)周式鬲特有的瘪裆开始出现,但似乎又具有一些传统形和中间形的影子;第三组,M62∶1(《晋中考古》图一三同的作风,又表现出商式鬲比较矮胖的特点,或已经混淆了两种形态的区别了。旌介M1∶25属于二谱系第三组是已经进入周初,还是在商末较多的接受了周文化的影响,目前尚难以解答。旌介没有三谱系陶鬲,但杏花墓地有发现,即M2∶1(《晋中考古》图一三四:4,本文图三)。该谱系陶鬲来自“高辿H1遗存”,这类遗存“陶质分粗陶和泥质陶两种……纹饰以浅、细及纹理散乱的绳纹为主,另有附加堆纹、指印纹、弦纹、划纹和雷纹,数量都不多,素面陶很少……陶器多为手制,鬲足模制,只有少量泥质器皿见轮修痕迹”瑧瑏。204年,在柳林高红(辿)发现并发掘的大型夯土基址瑏瑨,花边口沿鬲(图四)、空三足瓮、小口广肩罐、簋、小口罐等,充实了该遗存。不过,《204重要考古发现》发表的分裆鬲为商代晚期,《文物报》发表的鼓肩鬲,可能要晚到西周中期。在杏花遗址中,发现的H309:1和H309:2分别属二谱系的传统形和中间形(图二),H21:2、H304:1(《晋中考古》图一三〇:12、13)等(图三)属三谱系。H309:3(《晋中考古》图一三〇:9),折沿,沿唇上翘,口沿下施细绳纹,当为一谱系鬲,但此类鬲不多。已发表的白燕遗址H36:42(原报告图十六:15)属于一谱系鬲,这里还发现高辿H1遗存一类的墓葬,“可认为这类文化的居民,在和留存杏花墓地的居民存在着的文化联系外,还曾侵入到了后者占据的太原盆地”瑏瑩。这是我们今后应该